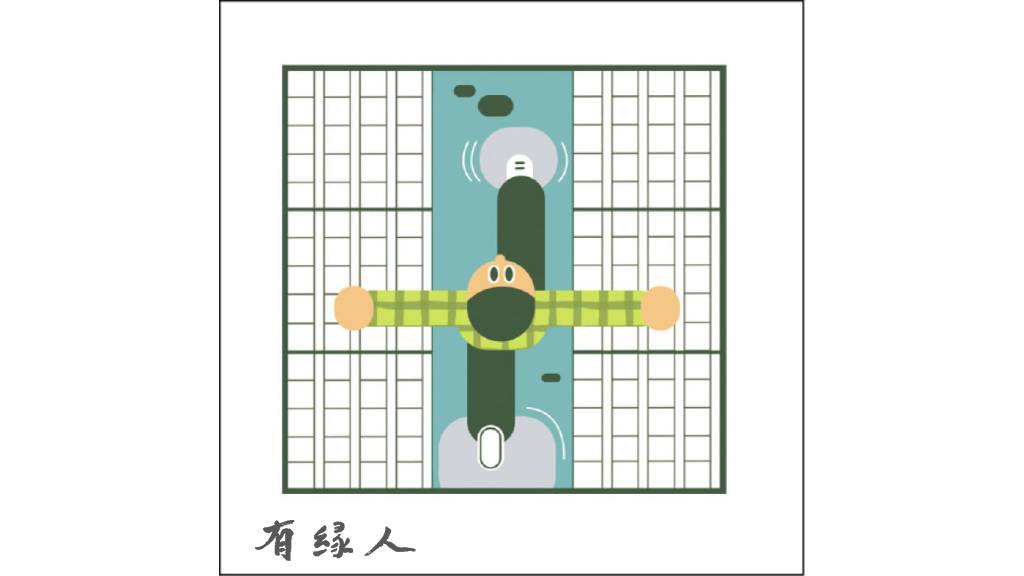
文/呂政達 圖/陳佳蕙
我的職業生涯,要感謝兩位貴人,這兩位都姓劉。
一位是作家劉克襄,那年他在剛創刊的《自立早報》當藝文組主任。有一天我接到素昧平生的劉克襄來電,要我去當藝文記者,竟這樣開啟我在自立報系漫長的藝文生涯。原因是我大學時代常往《中國時報》人間副刊投稿,他對我的文字有印象。我衝口問:「我不是都被退稿嗎?」劉克襄說:「大家有不同意見嘛。」也許那通電話,是要補償一個努力投稿的大學生吧。
另一位更早一點,是當時輔大應用心理系的老師劉兆明。原因是我在大一時寫了個不成熟的劇本,好像叫做《第二個春天》,取材〈桃花源記〉,還在系上由同班同學演出。劉老師聽說了我這個人,來系上任教就丟了篇英文要我改寫看看,我記得寫出來的東西取名為〈空間侵犯是把傷人的劍〉,如果多年後的我讀到那篇作品,可能會直接退稿吧,但也因此開啟了我《張老師月刊》另一段生涯路。
我雖然寫過生涯發展的書,主張過生涯規畫的理念,但我的職業生涯如同摸石過河,毫無規畫可言,就這樣混到現在,想起來只能說「好險」。
回顧所來徑,蒼蒼橫翠微。我感謝這兩位貴人,也許他們在我都不知道的時刻,看到了我的某些潛力。我也感謝已無從捉摸的、年輕莽撞的我,那時我還願意在多方挫敗後繼續嘗試,還憑著我從小養成的寫作興趣去衝、去叩門,感謝曾有過那樣的自己。
真的,如果我還能對「生涯發展」說一句真心話,我只能說,不要小看你小時候喜歡的、培養的興趣,那可能指出你將來的方向。我真的感謝當年爸爸在我小學生日時送的《格林童話》,又有點怨懟,為什麼沒有給我《如何賺到第一桶金》?
當我們自己握有機會的時候,願不願意也給一個年輕人同樣的機會呢?不是為了求回報或交易什麼,就只是把機會給出去。當年我在台大城鄉研究所旁聽畢恆達老師的課,他提到在美國求學時,他的老師如何幫助他,說:「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能不能這樣對待一個學生。」畢老師的博士論文寫的是〈物的意義〉,我在他的一堂課上體會著「人的意義」。
誰曾是你翅膀下的風,而將來有誰會在一篇懷念的作品裡提到你?
Views: 0
